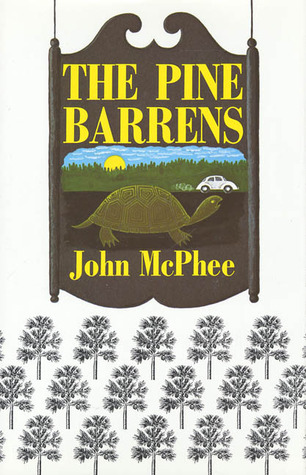去年九月搬到现在的住处,早就知道旁边有一片栅栏围起的菜园,因意大利同事夫妇曾提到他们每年都要种西红柿和罗勒。秋天频繁来往于两城之间,对菜园并没有半点好奇的念头。年初,小兔和猫咪都搬来我这里,总算又有了一个暂时的家。也许是三月的某一个周末,带着小兔在院子里散步,远远望见另一个同事E蹲在在菜园里,漂亮的金色卷发披散在肩上,旁边地上坐着的是还不会走路的小婴儿。小兔也注意到她们,我便上前问好。
“我在种豌豆呢,”E说,“再晚就赶不上季节了。”
看见小兔很感兴趣的样子,我问:“我们可以跟着你来学么?”
“你可以去领一块自己的地呀,”E说,“负责调配的一位邻居下个周末会来这边,我来介绍你们认识吧。”
“太好了,谢谢!”
一个星期后的周六上午,我迟疑地抱着小兔走向菜园,老远就看到里面已经很热闹了,一位银发女士戴着工作手套,正走来走去丈量菜畦之间的小径。几句交谈过后,她便指了菜园中央的一小块土地给我,并且在四角插上标杆为记。我望着满地杂草,问她:
“接下来要怎么做呢?”
她递给我一把钢叉,一具铁铲:“翻开土壤,把这些杂草连根拔出来……”
手起铲落,触碰到土壤的感觉先是坚硬,深处却柔软。初春的泥土绽开黝黑的内里,露出杂草白生生的根来,并且翻出灰红肥大的蚯蚓,转眼就向更深处逃逸走了。拔出杂草,抖落根上的泥,似乎有些是薄荷类的植物,手上鼻子里都是清香。小兔蹲在一旁,拿着一块土坷垃开始自顾自玩,一上午的时间居然很快就过去了。
一向自认养不活植物,却在这个寒冷的三月战战兢兢地开始想象自己的菜园了。似乎这片真正的土地,比花盆里的数寸空间要更宽容、更富探索的可能性。我们不是要供养一盆店里买来的花朵,而是从一片充满生命的生态系统开始,自己播下种子、自己收获。
“做这个对心理健康真的很好……”几天后,E又看到我来到菜地里干活,这样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。她来这里也有几年了,平时经常要自己照顾三个孩子,最小的女儿还不会爬,已经回到教书和研究的工作节奏上。
我菜地的邻居是一位已经晋升副教授的女士,家里养了五只猫,已经把家门口的阳台布置成一片生气盎然的小花园,迫不及待地要开始种蔬菜。从她那里分到了一些多余的种子,包括小萝卜和莳萝(dill),还有已经萌芽的一盆西兰花。和豌豆一样,西兰花和小萝卜都是耐寒的植物,需要在早春播种。我反复读了几遍种子包装背面简略的说明,就壮着胆子把西兰花苗和小萝卜种了下去。孰料过了不久便遭遇一场三月底罕见的大雪;雪后又回暖,等到过了几天再看,土壤表面都板结成了灰黄色,上面钻出了无数绿色的小苗,分不清那些是我要的蔬菜,那些是杂草……
整个四月,都在小兔、我和某人轮流生病的煎熬中度过。我有时记起来菜地的事情,过去浇一浇水,眼看着西兰花幼苗在恶劣天气和杂草夹击中伤亡惨重,小萝卜新生出来的叶子也迅速被虫吃掉。唯一欣慰的是莳萝这种本来就很像杂草的性格,从板结的土块中探出不少毛绒绒的脑袋。虽然对菜地的前景并不抱希望,但每天的生活仍然好像悄悄被改变了:开始以一种不同的心情去关注天气,每过一两天总要去菜地看看,和邻居聊一聊天,看着他们的豌豆爬满了架,还有淡紫色的芦笋在清晨悄然钻出地面。蚯蚓在四月的某个时候之后忽然消失不见,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小虫;野草的花样也不断翻新,好不容易认识了几种,又出现新的陌生幼芽。季节的细微变化好像就在这些具体的事物中被放大和突出了,时间流逝的质地也随之变得新鲜和有趣起来。
五月,终于结课,流感季节也告结束。在一个晴朗温和的早上,我送完小兔,又拉开菜地的栅栏门,决定无论如何,也要把我这一小片土地上的杂草给清理干净。别人家的西兰花已经长出非常茁壮的叶子,我却只剩下硕果仅存的五六棵幼苗,比三月时大不了多少,在清空了杂草之后,愈发显得瘦小。抱着一种穷有穷过法的心理,我决定任其自然。然而这几株伶仃的幼苗也终于慢慢长大了。
五月九号那天,我拔出了亲手种下的第一株成熟的小红萝卜,郑重地吃掉了它,发现味道清苦。莳萝已然高至及膝。怀着一点点微末而确定的喜悦,我开始筹划如何布置剩下的半块土地。
Labels: garden